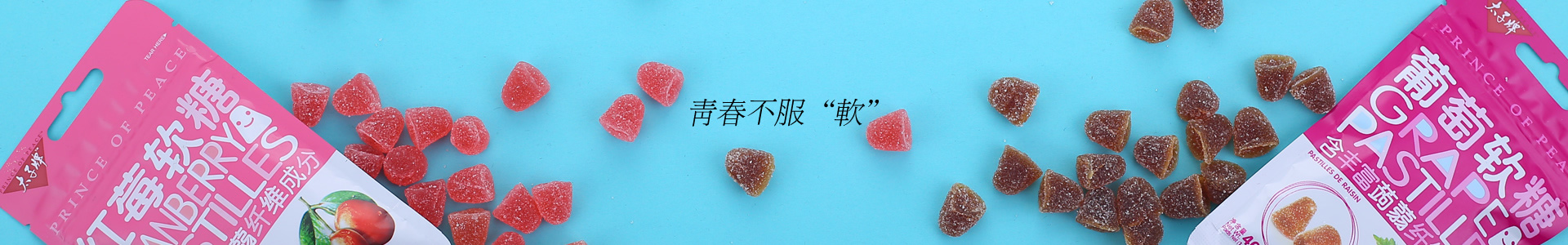新闻动态
毛主席尽管身体不适,仍毅然前往现场。
在灵堂内,毛主席留意到一副挽联,内容为:
仗剑守土为干城,忠心不渝。淮海传军威,江南留遗爱,万众同悲。望山河永别赤县,挥戈挽日豪气存。平生无愧,功在天下,九泉含笑。红旗遍新世界。

【不同流俗】
审视挽联内容后,毛主席大为赞赏,频频点头,称赞道:“写得很好。”
接着,他转身指向挽联落款人,询问陈毅夫人张茜:“此人是否已到?”
张茜闻主席之问,含泪摇头,为难答道:“他未至,因其身份敏感,故不被允许参加追悼会。”
毛主席闻言皱眉,张茜续言:“他们夫妇吉林归来,既无户口也无工作,生活陷困境。”
闻此言,毛主席沉思片刻,随即指示周总理寻得写挽联者,助其解决户口问题,并为其谋一份差事。

此人是谁,仅凭一副挽联何以引得毛主席如此?
撰写挽联者乃陈毅生前挚友,著名收藏家兼书画家张伯驹。
张伯驹系出名门望族,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中。
16岁时,他获推荐加入袁世凯的模范团深造。
之后,他相继在川闽两湖经略使曹锟及陕西督军张镇华麾下任职。
张伯驹身为名门贵公子,自然前程无忧。
然而,他在军中数年,逐渐觉悟军阀政治之黑暗,认为中国内外困局,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军阀。

因此,张伯驹不愿继续为恶行助威,毅然离职归乡,终日以吟诗绘画为乐。
张伯驹自断前程的举动,在上层社会中引起了广泛讨论。
张伯驹既不热衷仕途,也不喜好经商,在众人眼中,他是典型的不从事常规职业者,专注于非传统领域。
他与纨绔子弟不同,不爱享乐,不坐汽车,不嗜华服美食,不贪风月,不结交名流,与当时“上流社会”的作风大相径庭。
因此,许多人在背后议论他,甚至给他取了“张大怪”的绰号。
世人常误解张伯驹为游手好闲之辈,实则不然。张伯驹生活充实,勤勉有加,远非无所事事之人所能比拟。
他终身保持着一项爱好,即艺术收藏。这一爱好贯穿其一生,成为他不变的追求。

张伯驹鉴赏力出众,能迅速辨识艺术品的价值。
且遇心仪字画,则不惜巨资购入,因此收藏了诸多珍贵作品。
清王朝的终结,意外地造就了收藏大家张伯驹。
【守护文物】
王朝覆灭后,众多满清贵族逃难,为谋生计,不得不将家中书画古董变卖。
皇帝溥仪亦需变卖字画以维持生计。
张伯驹曾获悉,溥仪将宋代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与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两幅古董名画,送至银行作为抵押品。

银行经理犹豫不决,遂向张伯驹求教。
张伯驹鉴于文物价值,力劝经理收购,并自掏重金,将两幅画购回家中。
张伯驹起初收藏名画,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,并无他因。
他深入书画收藏行业后,对国家的现状深感痛心。
众多名画被藏家获取后,并未得到妥善保存,反而迅速被转售至国外。
洋人常趁乱抢夺中国宝物,手段包括威逼与利诱,肆意掠夺本属中华之瑰宝。
张伯驹对字画如此大规模的外流感到震惊,认为情况十分严重。

他认识到,若无人统一保护这些书画,中国珍宝终将落入欧美列强之手。
他暗自决心,将文物保护作为终身使命,致力于此。
彼时,张伯驹于字画收藏领域已声名显赫。
因此,众多卖家拥有名品字画时,皆首选张伯驹,而他亦几乎从不拒绝,一律接纳。
他尤其致力于保存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,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。
张伯驹为收藏字画散尽家财,众人不解,议论不断,更有猜测他意在囤积居奇,等待高价出售。

面对诸多争议,张伯驹仅以一笑回应,不予深究。
他收藏字画,旨在传承文化,非为谋利,源于身为中国人的责任感与良知。
1941年,张伯驹遭汪伪政府特务绑架。
特务致信张伯驹夫人,勒索300万赎金,威胁若不交,将杀害张伯驹。
特务们的意图是绑架张伯驹,以勒索其手中的字画收藏。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获取张伯驹珍贵的艺术品。
他们意识到古董字画价值极高,若销往国外,将为汪伪政府赚取大量钱财。
张伯驹深知字画若被特定之人所得,定会受损,遂告知妻子,即便自己命丧特务之手,也坚决不能交出字画。

特务因张伯驹一家不屈从,遂对张伯驹施加各种折磨,并不断发出威胁,企图迫使其屈服。
张伯驹坚持立场,与特务对峙长达八个月,期间未曾动摇。
八个月后,因社会舆论施压,特务被迫放弃原有条件,将赎金数额降低。
在各界的援助下,张家人集齐了40根金条,成功营救出张伯驹。
绑架案后,张伯驹虽心怀余悸,但保护字画的决心却更加坚定。
张伯驹这类真心为国者方能确保这些物品安全,若落入小人手中,它们将难逃流失海外的厄运。

张伯驹深知,文物一旦流失,追回极其艰难,且后代将无从探寻文化遗迹。
因此,张伯驹自此以防不测,常居书房,饮食起居皆于此,日夜守护那些珍贵的书画作品。
【高士之风】
张伯驹对贪财者宁死不屈,绝不妥协;然面对真正热爱书画之人,则慷慨大方,毫不吝啬。
王世襄对《平复帖》研究欲望强烈,但一直无法亲眼见到真品,深感苦恼。
后王世襄得知《平复帖》在张伯驹处,心中既感欣喜又存忐忑。
得知文物下落令人欣喜,但又忧虑张伯驹收藏家身份,恐其不愿轻易展示此宝贝。

两人素无交情,因此张伯驹未将宝物拿出,实属合情合理。
最终,王世襄鼓足勇气,向张伯驹提出借阅《平复帖》的请求。
张伯驹闻王世襄欲研《平复帖》,未做迟疑,即刻向其展示该帖。
王世襄借走《平复帖》后,经数月研究,著成《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》,对我国文物研究贡献巨大。
1956年,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形势日趋稳定。张伯驹目睹此景,内心充满喜悦。

他毅然决定,将自己珍藏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,以此作为重大贡献。
张伯驹收藏的古董字画,众多均为国宝级文物,每一件都拥有极高的价值,堪称价值连城。
变卖其中任意一件藏品,张伯驹便能确保自己生活无忧。
多年来,张伯驹尽管生活困顿,仅以粗食度日,却从未萌生变卖藏品的念头。
现今,他慷慨无偿的捐献行为,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。
沈雁冰任文化部部长时,得知情况后提出,张伯驹多年致力于文物保护,功绩显著。
因此,建议以20万元的价格,购入张伯驹所持文物。

但张伯驹听闻后,拒绝接受。
他反复强调,所收藏的文物本就归属中国人民。
在国家危难时,我代为保管此物,今赠予博物馆乃物归原主,因此,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。
在张伯驹的执意捐献下,故宫博物院最终同意接受其无偿赠予的文物。
张伯驹仅接受文化部颁发的奖状,其上书八字:“化私为公,足资楷式”,以此表彰其贡献。
1957年,北海举行明清书画展,热爱字画的陈毅抽空前往参观。

陈毅在现场介绍人的讲解下得知,众多字画里,张伯驹慷慨捐赠了其中大部分。
陈毅闻后,对张伯驹深感敬佩。展会归来,他即邀请张伯驹至家中做客。
两人因共同爱好相投,交谈甚欢,话题不断,彼此意见契合,交流十分顺畅。
【知己之情】
陈毅就收藏方面的诸多问题向张伯驹虚心求教,详细询问并获取了专业解答。
张伯驹对陈毅的潇洒旷达深感钦佩,尽管相识时间不长,两人却迅速成为知己。
一年后,张伯驹竟遭遇变故。

张伯驹不仅热衷于收藏字画,还是个京剧迷。
他与一群热爱京剧的票友共同创立了国剧社团,旨在推广京剧文化。该社团组织有序,致力于传承与发展国粹艺术。
同时,编排了一出名为《马思远》的戏剧。
这出戏竟引发众怒,众人指责张伯驹排演目的不纯,有颂扬封建之嫌,更有人提议将其划为右派。
陈毅闻此事大为愤怒,言:“张伯驹乃文人,且为国捐赠众多,岂能是右派!”
张伯驹对此事颇为豁达,称:“帽子无所谓,我乃凡人,生死得失不影响大局。若说我反动,实属冤枉。”

外界流传的流言蜚语,对张伯驹的生活造成了显著影响。
1961年,陈毅因常感担忧,特地寻访吉林省委书记,请其于吉林博物馆为张伯驹谋职,以使其远离纷扰。
张伯驹携全家迁往吉林,并担任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一职。
张伯驹离京之际,陈毅前来送别,确保他不受丝毫委屈。
张伯驹保持乐观,对陈毅言:“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委屈难免且微不足道。我鉴画亦曾出错,为何不容他人误赠我一顶帽子?”

尽管陈毅努力保护张伯驹,但张伯驹仍于1966年被冠以反革命之名,被迫离开博物馆,遭下放至舒兰地区。
然而,舒兰方面对张伯驹不了解,颇有微词,有人甚至直言:“这位70岁的老者,难道要我们赡养他吗?”
对方态度如此,舒兰无法继续留下。张伯驹与妻子万般无奈,只得重返北京。
归来后,发现昔日居所已易主。
张伯驹夫妇因无户口和工作,最终仅能寻得一处十平米小屋作为安身之所。
一家人在北京生活艰难,吃穿难以为继,幸得亲朋好友不时援助,方能维持生计。

陈毅获悉老友遭遇困境,内心极度痛苦。
陈毅当时亦受诸多指责,虽欲解救张伯驹于危难,却力有未逮。
因此,陈毅随后拜访周总理,恳请其协助为张伯驹安排职务。
然而,在事项尚未实施之际,陈毅因病情加重而入院治疗。
1972年陈毅去世,张伯驹得知后深感悲痛。他心情沉重,对这位老友的离世无法接受,情绪极为低落。
张伯驹申请参加陈毅追悼会,鉴于其身份特殊,申请遭拒。
张伯驹深感郁闷,忆及陈毅生前的诸多帮助,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为陈毅尽一份心意。

因此,他挥笔创作了一副挽联以悼念陈毅,并嘱托他人将这副挽联带至追悼会上。
张茜目睹挽联,心中涌起感慨。
她了解丈夫生前极度钦佩张伯驹,故特意将挽联置于灵堂醒目位置。
机缘巧合,毛泽东主席留意到了那副挽联。
听完张伯驹与陈毅的故事后,毛主席认为,张伯驹过去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。
因此,毛泽东立刻决定,为张伯驹分配职务。
至此,张伯驹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。他的日常开始变得有序,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规律,中心思想与生活状态均得以保持。

张伯驹历经多次起落,却始终保持淡然态度,不为所动。
张伯驹论及挚爱的书画收藏时表示:“我所收藏,不求永伴我身,但求长留故土,世代相传,有序不乱。”
中国文明网刊文《张伯驹的文化精神与家国情怀》,深入探讨张伯驹的文化贡献及深厚的爱国情感,彰显其精神风貌与对国家的深情厚谊。